新書 | 站在比青藏高原更高的精神高地——《拉薩河的色彩》

用 生 命
詮 釋 崇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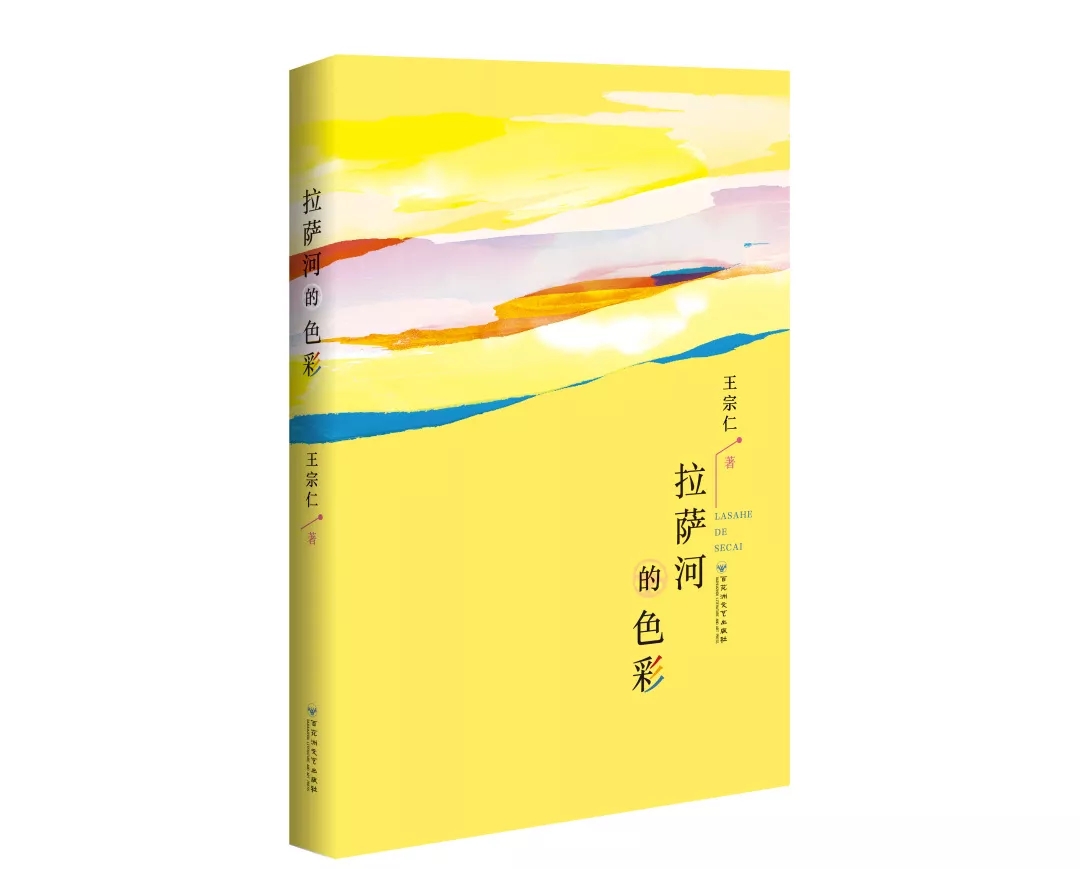
《拉薩河的色彩》
王宗仁/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定價:43.00元
編輯
推薦
《拉薩河的色彩》以平樸的敘述加上詩性語言的插入,意境高雅,富于感情底蘊。全書敘事結構獨特,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故事性和畫面感極強。作者的身份很特別,他是作家,又是當年奮戰在青藏高原的英雄。在作品中,他既是故事的講述者,也是故事的親歷者或目擊者;既是寫作者,也是被寫者。這種雙重身份的書寫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沖擊力。
內容
簡介
《拉薩河的色彩》一書把我們帶到遙遠圣潔的雪域高原,帶到極具時間跨度(最早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唐古拉山,讓我們結識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平凡中見偉大的人(最難忘那些超凡脫俗的年輕女性),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生命的意義,領會到“崇高”的豐富內涵。
作 者 簡 介
王宗仁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青藏高原當了七年汽車兵,出生入死,上百次穿越險象環生的唐古拉山到西藏。在逼仄的駕駛室里堅持寫作。由于文學上的突出才華,奉調解放軍總后勤部從事宣傳工作。中國軍旅文學的大家和中國散文界的宿將,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對于王宗仁來說,當汽車兵穿行于青藏線的七年刻骨銘心。身在京城,心系高原,像朝圣一樣,多次回到唐古拉山,回到格爾木,或收集寫作素材,或探訪長眠的戰友。在他的心目中,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是圣潔的“精神高地”。幾十年來筆耕不輟,出版文學書籍四十余種。青藏高原始終是他的創作母題。
自序:總會有一顆星在我頭頂閃爍
常常有人給我提問:你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就那么心甘情愿嗎?坦率地說,苦、累,甚至對生命的威脅都時刻存在。但我愿意面對。只因為我內心有一個難以抑制的支撐:一心要當作家。
14歲那年,上小學四年級的我寫了一篇命題作文,我長大后的志愿是要到青藏高原去,當一名勘察隊員,成為作家。為什么要把去青藏高原和當作家聯系起來,當時我說不清楚,就是現在愿望變成了現實,我也道不出個所以然。反正自從在課本上知道了中國西部有這么個美麗富饒的青藏高原以后,就把它牢牢地放在心窩里了,常常做夢都到了那里。還是好奇多于理智。記得有一支歌曲《勘察隊員之歌》,好讓我喜歡,莫名其妙地覺得那些勘察隊員都戰斗在青藏高原,我常常哼唱著,有時走路也用腳和著節拍哼唱: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是那天上的星,/為我們點燃了明燈;/是那林中的鳥,/向我們報告了黎明;/是那條條的河,/匯成了波濤大海……

我想象勘察隊員在冰天雪地高原上的生活,勾畫著我的作家夢。
也是14歲那年,我的處女作《陳書記回家》,在1955年第8期的《陜西文藝》發表。農村小娃娃在省級文藝刊物發表作品,確實罕見。我很得意,這篇作品的問世,縮短了我想去青藏高原當作家的距離。我的心更急切地飛向那個遙遠的地方!
滿天都是星星,總有一顆在我頭頂閃爍。
生活中的巧遇常常不期而至。1957年冬,部隊到我們縣里接兵。當時我并不知道接兵接的是什么兵種,更不清楚他們駐扎的地方在哪里,許是企盼走出農村的心情太急切,就辭掉了在一些人看來很不錯的民辦教師的工作,瞞著父母報名參了軍。鋪著稻草當床鋪的鐵皮悶罐火車,把我們這些還穿著老百姓衣服的新兵拉到蘭州,又坐了四天的敞篷卡車,來到昆侖山下的汽車團。從此,我當上了一名高原汽車兵。我夢寐以求的上青藏高原的夢想,真的好像做夢一樣,就這樣似乎輕而易舉地成為現實。作家夢呢?我卻感到有些迷茫,但并沒有斷了念想。我相信和她畢竟有著可以用心靈交流的秘密。暫且將這顆早就孕育的文學種子埋在心底最肥沃的寶地,一場春雪飄來她會發芽!
直到我在汽車教導營學會了駕駛、修理汽車技術,第一次開著汽車從插在格爾木轉盤路口,標志著“南上拉薩、北去敦煌、西往茫崖、東到西寧蘭州”的路牌前起步,駛上2000公里青藏公路時,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實現作家夢想的路開始了。我強烈地感到可以從這個四通八達的路口攝取足夠的養分以滋養我的夢想。此刻,1959年初夏,一場“六月雪”正降臨昆侖山。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雪,除了矗立的雪峰,就是被白雪幾乎填滿了的洼地。我特地剎住車,走出駕駛室朝通往四方的路上眺望,雪峰連綿起伏。近的那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把雪;遠的那么遠,可望而不可即。瞬間,我想象的翅膀隨著這通往四方的遠路展開,飛翔起來。我能走到我需要去的每個地方嗎?未見得!生活中常常能遇到格爾木這樣的轉盤路口,你有時趕路的步伐越快反倒越容易迷惘和走失。不是嗎?如果是逃路的人,保不準走著走著,腳印倒是種在了路上,前面卻是一個又一個墳頭……生活就是這樣,找到一些謎團答案的同時,又引出了太多的懸念。你又不得不朝前方走去,再尋找。
我正這么想著,一陣來路不明的雪,被去向不明的風吹動,幾個牧羊人趕著羊群不知該走向哪兒……
無意間,我發現路邊的雪層上挺立著幾叢荊棘,在這野性的荒原上,它默默地吮吸著積雪用過的陽光。正是它們守住了原始的蠻荒。
我采摘了幾叢荊叢,這是詩心文眼。
飛雪和冰凌在方向盤上交匯,山路和戈壁在掌心重疊。敦煌、陽關、日月山、倒淌河、納赤臺、昆侖神泉、長江源頭、拉薩河谷、布達拉宮……這些令多少人神往的鮮活得冒著仙氣神韻的名字,是求之不得的文學原生態素材,從我踏著汽車油門的腳板下,一次又一次地閃過,刺激著我的神經,勾撞著我的魂魄。運輸任務繁忙,經常白天黑夜連軸轉地跑車,我只能利用開車中點點滴滴的空隙時間,見縫插針寫稿。但是我真的寫不好,只能乘著夢的翅膀回到駕駛室坐墊上,把所見所聞的事記在隨身帶的記事本上。創作需要走進生活,更需要靠近歷史。于是我搜集我所在的汽車部隊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故事。我堅信,一個人如果有一把萬能鑰匙,就會有十萬把能開的鎖子。這么多豐富多彩的文學原料,還愁變不成散文!
文學的路比我開初想象的遠還要遠。我寄出一篇又一篇散文,還有詩歌,天天等待開花結果。好不容易盼來自費訂閱的報刊,戰戰兢兢地打開目錄,尋找自己的那盞燈,可是看到的都是別人的名字。我的燈卻不知在哪個幽巷里蟄伏著。
往事不可假設,但未來是可以預測的。我踩油門的腳踏得更狠勁了,恨不得一腳就踏出屬于自己的一本書!我把那些親身經歷的,親眼看到的,還有從歷史深處挖來的文學的夜明星、五彩路,繼續詳略得當地記在記事本上,積攢著,再積攢著,等待著爆發!
我一直不相信文學創作有一種永恒的理論,但我們還是需要它。在一些創作階段,只有理論能廓清我們的思想,讓我們從迷亂和人云亦云的混亂中輕松走出來。忽然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貴人,至今我都記得他的名字。其實說不說他的名字有什么重要,他只是一個文藝刊物的編輯,叫“師日新”。今天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個名字。他來高原深入生活,得知我癡迷文學,寫了許多作品苦于發表不出來。他特地見了我,說了一番話,至今我記得大意是,文學創作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想象藝術,最可貴的是創新。好像畫家面對一張紙,下筆的地方有十個、百個,以至千個。到底能下筆的地方有幾個,完全由畫家自己。說實在話,他的話我當時似懂非懂。他還特地給我講了詩人李瑛的幾首詩。幾十年來,我一直記著師日新老師的指點,摸索前行。他是在啟迪年輕的作者,要熱愛生活,但還要走出生活,生活在文化里。這樣才能做到既源于生活,又能高于生活。文藝創作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的藝術,豐富是用來贊美簡約的。
開車和寫作是我成長中并蒂的兩片綠葉,共享陽光,同浴風雨。我的那個記事本怎能不像口袋呢,里面裝的是釀制文學的精米細面。我匆匆趕路,忙忙往里面填充,最后把自己也裝進去了。

誰說通往春天的路上不是布滿荊棘,汽車駛進昆侖山后,山體上不時有泉水飛流直下。昆侖神泉是不是相傳的當年文成公主進藏路上洗理自己的梳妝臺,另當別論。但是眾人皆知這泉水最嫩的時候是大雪封山的季節。我的文學生涯在封閉和寂寞的意境里,經過相當艱難而幸福的跋涉,終于在這里亮起了一盞燈。
散文《昆侖泉》在1964年第6期《人民文學》發表。我接到這期刊物,無法掩藏的心花與剛剛落地軍營外的春光接壤。不足2000字的一篇短文,速寫了高原汽車兵和養路工人攜手共守疆土的深情厚誼。一瓢水同樣可以滋養根的生命。它給經過多少輪回才找到一盞燈的我,帶來的沖擊波是突破性的。整個春天,再加上整個冬天,我的心都是熱的。怎能不熱呢?就在不久前,也就一個月吧,我創作的反映高原汽車兵生活的散文《考試》,在全軍舉辦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新人新事”征文中獲獎。這篇散文只有1500字,小散文折射的是大道理,它記述了汽車部隊打破傳統的考試模式,進行路考的新的考試方法。半年前,我把《考試》的手寫稿工工整整地謄抄在公用信紙上,寄到征文辦公室,不久就在《解放軍報》文化園地副刊發表。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它會獲獎,驚慌大于喜悅。獲獎證書寄到高原后,團政委王品一在全團干部大會上,把獎狀高高舉過頭頂,自豪地說:“這是總政治部發的獎狀呀!”至今,我依然十分珍惜地妥善保存著這個銀色燙金、蓋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紅色大印的獎狀。
差不多與《考試》獲獎的同一個時間里,我的另外一篇散文的發表,不但驚動了汽車團,還讓我家鄉的親人也著實受了一場虛驚。確切地說,那只是一篇小故事,題目《風雪中的火光》,發表在《解放軍生活》上。內容真實地記述了我們的汽車被突降的暴風雪圍困在唐古拉山上。零下30多攝氏度的氣溫,滴水成冰。為了保護汽車的水箱不凍壞,我們把棉軍衣的棉絮甚至衣面都撕下來,蘸上柴油點燃烤車。文章的最后這樣寫道:“第二天早晨,暴風雪停了,我們重新上路。這時候,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只剩下線衣和單衣。我們把溫暖給了汽車,為的是讓它去溫暖西藏人民。”那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聯播》之后的《解放軍生活》節目,轉播了這個故事。軍營的戰友們都聽到了,我家鄉的親人也聽到了。母親得知我把棉衣生火烤了車,擔心我會挨凍,趕做了一件棉背心,讓父親寄到部隊。父母疼兒的愛心可以理解。我接到背心后,一直舍不得穿,只是在每次乘車路過唐古拉山時,特地穿上它,以留住那個發光發燙的歲月。
《昆侖泉》發表后,1966年第7期《人民文學》又發表了我的第二篇散文《夜夜紅》,依然是反映高原汽車兵生活,但是無論從取材的角度及揭示生活的深度,還是對高原汽車兵在高寒地區執勤中的奉獻精神,及面臨的困境,物質匱乏和精神富有的反差,都有了比較敏銳的微察和細取。
需要說明的是,《昆侖泉》和《夜夜紅》都是被兩家報刊退稿后,我再次做了較大的修改,才得以在《人民文學》發表。我總相信,失敗無處不在,成功就在你的身邊。只等你去喚醒,冬去春來。
一個汽車兵的作品,接二連三地在全國全軍報刊上發表,引起人們的關注是不奇怪的。蘭州軍區文化部尉立青在1965年第1期《青海湖》發表了《可喜的收獲——評王宗仁的三篇散文》,文中寫道:“這三篇散文篇幅都很短,但很精。作者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極力地歌頌了高原的新風貌和高原人新的精神狀態,使作品充滿了熾熱的時代激情和強烈的時代精神,可以說是三篇較好的散文。”這三篇散文除了《昆侖泉》之外,還有發表在《青海湖》上的《船》和《昆侖雪里紅》。
說起尉立青,還有個有趣的小插曲。他來高原深入生活,同時為《連隊文藝》組稿。他特地約我寫一篇散文。我加班寫了篇題為《裴大嫂》的特寫,頌揚了某兵站一位裴姓男招待員熱情、細心、周到地為過往兵站的指戰員服務的故事,大家都親熱地稱他“裴大嫂”。尉立青編稿時把文中的“他”都改成了“她”。編完后才恍然大悟,又把“她”全部恢復成“他”。他很風趣地對我說:“大嫂也可以是男人。我只好讓‘她’回到男人的行列里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遠方,渴望當作家的我對遠方的渴盼似乎比一般人更強烈。遠方不在起點而在盡頭。盡頭到來之前,它在哪里,好像很難一語道破。如果把你的遠方比作燈火,這燈火掛得比星斗還高。你可以做到的是,雙手要緊握陽光,不讓它從指縫間滑落。1964年前后,我感到我離遠方好像靠近了一步。只是靠近,遠方并沒來到。這個時間段,有三件喜事突然敲門,讓我興奮。一是我和我的同鄉同學,同年入伍又同是汽車兵的戰友竇孝鵬,攜手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協會。二是西安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王積成來高原組稿,約我和竇孝鵬創作一部反映高原汽車兵生活的電影劇本。我倆一聽就嚇炸了,寫電影劇本?做夢都不敢想的事!王積成告訴我倆,只要拿出初稿,他們會有人幫助完成任務。三是我把多年來發表的散文冠名《青藏線上》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希望能編入正在全國讀者關注的“萌芽叢書”。分社收到書稿后編號登記,讓我等待處理意見。
青藏高原四季落雪,雪落下來就會融化,融化后冬天就單薄了。不能不說,我的文學夢可以望得見“遠方”在地平線上恍惚出現幾縷曙光。雖然我明白,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滿懷希望地盼望著奇跡終于會出現,讓可能成為現實!
我又一次堅定信念,又一次抬起頭踏上了茫茫青藏線!

最終,后面的兩件事八字沒見一撇就飛了!“文革”的戰車碾過的地方,遍地都是光芒,但沒有人知道這光芒有幾多綠色,在這連森林也發呆的日子里,我偶爾也會望著幾片枯葉想象我的“遠方”。回憶失落的美好,反而讓我長時間抱有希望和期待。我便嘗試著恢復失落的、有點殘缺的文學夢。因為生活總是給我們帶來驚喜,誰愿意看著原本多彩的日子變得死灰一樣寂寞!
積累昨天的經歷,創造今天的歲月,奔向明天的“遠方”。
我繼續創作,我真的巴不得將在風雪路上開車經歷的故事,以及沉淀在腦海里的文學功底,都傾注到拉薩河里,用它的寬闊和流長孕育出一篇美麗的文章。沒有發表作品的陣地——“文革”中所有的文學刊物以及報紙都停刊,或者改頭換面,我的筆記本就是陣地。記的內容大都是我寫“我”,又是在自己的陣地發表,在寫作技巧上進行一點探索,甚至展現一些時代的盲區,野一點也無妨。一篇又一篇散文、詩歌,甚至報告文學,謄抄在我自備的大小不一的筆記本上,有的本子是很精美的印著“最高指示”的獎品冊,有的是我買來的有副統帥舉著語錄本頭像的紀念冊,還有的是我自制的用畫報包封皮的筆記本……我把它們統統稱作“學步集”,一集、二集、三集……至今我仍然保存完好。我的許多散文就是從這個陣地上長出來的,我說“長”,是因為那些記下來的事情,僅僅是根,給它們添枝加葉后,就成了作品。那個隆冬,我在楚瑪爾河畔寫下一篇紀事后,看見河邊孤獨的凍土和叫不上名字的卑微的草根,獨自承受一種凜冽,不知為什么我總想回頭,走到文學的起點上去。也怪,就在我回過頭的一瞬間,看見了“遠方”的那盞燈還在閃爍。于是,我又把頭收回,靜靜地貪婪地望著記事本里那些文學“胚胎”。
我在創作上的一個明顯的拐點,或者說又一次爆發出火花,是1974年初春。當時我已經調到北京,在總后勤部宣傳部任新聞干事,文學創作是業余愛好。平心而論,我調到北京從事新聞工作,主要還是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成績幫了忙。1985年1月13日,我在《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我的兩駕馬車》,這兩駕“馬車”就是新聞和文學,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我的肩上拉著兩套馬車。我酷愛文學,也偏愛新聞。八小時之內寫新聞,八小時之外搞創作。拉兩套‘馬車’當然要比單槍匹馬費力了。但我心甘情愿……我總覺得離開新聞工作崗位,也許我的創作也會隨之枯萎。”
話題再回到1974年初。一天,一封帶著青藏高原早春暖雪的信飛到我手里,是剛從《青海湖》編輯部調到青海人民出版社當編輯的楊友梅的來信。她在信上寫道:“我很喜歡你寫青藏線生活的散文,一直有個心愿,想把你這些作品匯集成一本冊子,由于種種原因始終未能實現。現在看來這項工作可以著手做準備了,請你把你的作品整理出來,寄給我看看……”
我驚喜得心都快蹦出胸膛了!我,一個曾經在風雪青藏線上開車的司機,幾次送稿和她見面時都是穿著油膩的工作服,她接過稿件總會客氣地讓我坐在沙發上,詢問我們汽車兵的一些情況。之后她就埋下頭看我的稿,邊看邊用筆在上面勾勾畫畫。我總覺得我雖然坐在她身邊,但離她那么遠。哪里會想到她現在突然提出要給我出書,而且還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她在信中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集子里的作品必須有一半以上是新創作的,未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過的。我立即很興奮地給她回信,詳細談了對要出版作品的設想,列了個提綱。從此,西寧—北京之間的信件頻繁傳遞著創作信息。我每寫出一批作品就捎給或郵寄友梅老師,請她指教。她從來不積壓我的稿件,看完后總是及時和我聯系。她對作品的標準要求很高,我新創作的或修改的作品,她總要提出進一步修改意見。
其間,有一件事我是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它多少也影響了我的寫作情緒。她退回了我點燈熬油新創作的七篇散文,幾乎全部否定。我把她長達5頁的信反復看了好幾遍,心中的不快和委屈才漸漸消散。信中她詳細地談了每篇散文的不足之處,并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后來被教育部選入全日制十年制學校初中課本語文第三冊的散文《夜明星》,原文中有一段關于天葬的文字,她提出正文中有“天葬”二字就可以了,不必展開寫,在文后加注釋。天葬是藏族宗教信徒處理死者遺體的一種獨特做法,三言兩語在正文中很難說清楚,也沒必要。她的意見是對的,我照辦了。友梅老師還提出,將七篇散文中的兩篇散文合二為一。她在信末寫道:“我既然要給你出書,就會嚴格地要求你。”很快,我按照她信上的意見,對七篇散文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調整。寄她后,她又熱情洋溢地回信,稱贊修改后的作品不僅內容充實了,也有了較深刻的意境。她還高興地告訴我,她編的工人作家程楓的小說集征訂數為275000冊。希望我這本書的印數也達到這個水平。
友梅老師在這期間常常利用她愛人老羅來京出差的機會,順便給我捎來她改好的稿件讓我謄抄,我則把修改好的稿件讓老羅捎回。老羅每次都和我約好在我們部隊駐地的萬壽路地鐵口見面,不見不散。老羅人很瘦,樸實,淳厚,話不多。我多次請他到機關坐坐,他總是笑笑,說很忙,以后有機會。可是,他始終沒去。我每次見到老羅,總覺得他滿臉憂郁,像有很重的心事。
當時,我怎么也不會想到,老羅就是“胡風集團”的那個成員羅洛,我只知道他叫“羅澤浦”,我們都喊他“老羅”。十多年后,當“胡風集團”的冤案得到平反,羅洛也恢復了名譽,成了上海作家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一本又一本詩集像噴泉一樣涌了出來。楊友梅也回到上海,在《收獲》雜志社工作。回首往事,我真是又吃驚又不安。我仿佛做了一場夢。但是,一切都是真的。1975年11月《珍珠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
至今,我已經出版了45本作品集。
2008年4月,我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散文集《藏地兵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散文集是當時素不相識的年輕編輯丁曉平找上門主動向我組稿的。他在書的封面上赫然寫著這樣的導讀語:“比小說更精彩,比傳說更感人。一個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軍人,一個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寫了四十多年高原軍營生活,有數百名藏地的軍人從他筆下走過。大家稱他‘昆侖之子’。”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有一半以上是經過《解放軍文藝》的編輯王瑛精心指點發表的。她告訴我:寫青藏高原軍營的題材,是你獨有的文學資源,但是你不能只憑簡單的經歷和經驗寫作。當然,這樣寫也容易打動讀者,卻也容易失去個性,往往淹沒在共性的洪流之中。她對我說,“你不僅要站在自然的海拔高度寫高原軍人的苦樂、死亡和愛情,還要站在人性的海拔高度去寫。”她打了一個比喻:“如果你拿個碗在瀑布前接水,能接到水嗎?”
我理解并踐行王瑛的這番點撥,直到今天。優秀作品的產生不僅需要時間,更重要的是要改變對生活的思維模式,以及如何取舍生活,把原味生活釀制為文學作品。之后,我在探索摸索中創作了一批散文,不但取材有突破,寫作也有了與過往不同。以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的三篇作品為例:
《傳說格爾木》,寫了一位藏族老阿爸為了保護埋葬在戈壁灘女軍人的遺體,赤手空拳與毀墳的野狼進行搏斗。他硬是用青筋暴起的拳頭砸死了張牙舞爪的野狼。女軍人是因為缺氧斃命的,老阿爸也是因缺氧獻出了生命。女兵墓旁又立起一座新墳。《情斷無人區》,展示了平息西藏叛亂中,發生在藏北無人區一樁離奇、悲涼,卻引人深思的愛情故事。追殲叛匪頭目的戰士和匪首女兒,在無人區邂逅,碰撞出愛情火花,成婚、生子。后又各奔東西,女人進了尼姑庵,遺落在無人區的丈夫仍在等待、尋找藏女。《唐古拉山和一個女人》,反映了青藏線上第一個漢族女人給軍營帶來的滿園春色,而她自己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后來,王瑛隨我走了一趟青藏高原。她在和我的一次對話中說:“我上一次青藏高原,看見的青藏高原是一種樣子,您年年上青藏線,寫出的高原故事又是一種樣子。生活和文學的這兩種樣子在記憶里重疊在一起,您對青藏線上官兵生活的感受,變為對生命在極限狀態中所呈現的光輝的一種認知。而這正是文學不可替代的價值。”
也許,今生我再不可能上青藏高原了。但是,我還會寫高原生活。因為文學,讓我站在了比青藏高原更高的精神高原上!
2019年春節于望柳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