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歷史的明鏡啊,宛如不落的皓月,
高懸在天地之間,其光輝為三教之源,
萬年未有分毫略減,啟發著圣者先知
去指點眾生,或蒙蔽天下。
請神明把時光的長河,倒流回元末的
至正二十八年春,若眾生能有幸開目投望,
便可見逐鹿得手的洪武大帝,
正躊躇滿志在議制萬歲的龍衣,
欲登他萬年的朝基,而橫掃歐亞的
蒙古朝廷,像折翼的鷹威風不再,
瞬間便把這萬年夢碎成一地華麗的瓷片,
如同以往所有的朝廷末代,狼狽逃出大都的皇宮,
似敗獸遁回草原,蜷在蒙古包里驚魂未定,
舔著血淋淋的巨創不甘罷休,
指望著擴廓帖木兒和他的人馬勤王護國,
卷土討還那中華的花花世界。
元室河南王和中書左丞相擴廓帖木兒
統轄的山東大地,被朱家征虜將軍
徐達和常遇春統領的二十五萬戰騎和步卒,
火蟻般密集攻城掠地征戰已畢,
大軍埋掉數萬猶如死蟻的尸骨,
當作齊魯焦土復蘇的肥料,
去催生供養新朝的稅苗,并豎起新王的
獵獵朱旗。新旗下,接往大洋的半島膠州板橋鎮的
大港鞭炮齊鳴,在慶賀華夏族的光復,
也是這里商船祈求海神庇護的聲音。
一行沉甸甸的貨船,滿載鎮上百家的生計指望,
即將揚帆遠赴萬里浩波之外的波斯,
久經風浪的船主展老大神色自信,
在碼頭與妻兒徒弟和水手們面朝大海,
叩頭禮拜,虔誠上香。
一隊軍馬疾馳而來,為首的是鎮守此地的將領,
赫赫有名的鐵弓神箭百夫長匡福大人。
展家獨子展雄聞聲看去,
這十五歲的少年羸弱又稚氣,
不知道自己即將成為奴隸和巨鯨的主人,
匡福大人也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
將與這少年緊緊相連,
而故事的大幕就由此驟然拉開。
匡福翻身下馬,纓盔鐵甲,閃閃發亮,
他此刻焦急趕來,怕的是商船遭遇不祥,
只為日本南北戰亂,流寇成群,劫掠成常,
這里是登陸中國最近和相對繁華的商埠,
倭寇們覬覦的賊目,早已密布海上。
將軍來到恭迎的展老大面前,拱手執禮,
建議派一隊軍船,護他百里海航,
鐵弓神箭訓練出的好箭手,船上也能百步穿楊,
而商船載著鎮上百戶人家的希望,若遭賊手,
百姓元氣損傷,百夫長也愧對君王。
展老大卻有他的主張,只為見慣舊朝元將的嘴臉,
未敢輕信新朝的官家,他臉上帶著笑,
心里卻不肯買賬,對將軍還禮,也要安撫四周送行的
鎮民和股東。他丹田提氣,不卑不亢:
“將軍好意,展祥沒齒難忘,草民祖上是大宋御前
帶刀護衛展昭公,草民雖無其全部絕藝,
也與徒兒習得幾樣,韃子當朝,倭賊便時囂張,
若無把握,安敢萬里遠洋,還把唯一骨肉帶上?
即便草民這番遇上,船上刀斧,也不致辱沒祖上,
還請莫分兵力,安守板橋百姓,安守膠州海疆。”
股東們紛紛點頭,嘴里嘖嘖贊賞,
同時竊竊交耳,認為匡福必有圖謀,
難免與貪財的韃子官兵一樣。
匡福還想解釋,展祥已不容置辯,發出號令,
水手們雀躍登船,解纜起錨,把匡福晾在一旁,
少年展雄,也匆匆與噙淚的母親作別,奔上甲板,
憧憬地看向父親和水手們時常描述的奇詭遠方。
賬房王繼謀察言觀色,看匡福神色不悅,
湊來對他賠笑:
“大人勿怪,我們已去過幾次波斯,
曾經過山一樣的大浪,見過山一樣的鯨王,
還遇過通身漆黑的夜叉鬼,都沒能把我們怎么樣。
展老大也確實有所依仗,因為上次回來遇到強風,
船被吹離了老航道,他卻因禍得福發現新航線,
這番出去,便行此路,倭賊難知其詳。
待我回來,定去大人府上問安,大人想要什么,
在下走遍波斯也為大人尋訪。”
匡福無奈地走去,上馬率隊歸營,
路上心神不寧,唯能暗暗禱告,同時默默思索,
如何讓這里的百姓,與自己同心無間,
一旦賊寇來犯,能夠軍民抱團抵抗。
而商船升起高帆,在眾人的目送下依次離港。
展祥掌舵領航,令展雄把手試舵,
少年感覺到大海的無邊力量,頓時一臉蠟黃。
展祥皺起眉頭,目光嚴厲又慈祥:
“這番帶你出洋,你娘還眼淚汪汪,
看你這瓜秧似的身架,不跟我來海上歷練,
往后怎能為展家頂起大梁!從今日起,
別再嬌氣,去波斯來回這兩萬里,
你就是水手,就是船工,不把骨頭練硬朗,
沒個山東漢子的樣,就別回家見娘。”
展雄出洋只圖新奇,并不想聽父親的這些教訓,
借口解手離開,去看海上魚飛鷗翔,
而這些都不算稀罕,就慵懶去曬太陽。
父親瞥見,喝叱聲像空里落下的雷鳴,
他打個激靈,悻悻拿起工具做個模樣,
叱罵聲消,又伸個懶腰鉆進睡艙。
船工們看了搖頭,展祥更暗暗煩惱,
只希望他能在兩萬里的風浪中逐漸成長。
船行百里,大陸早已隱沒不見,
忽聽水手們陣陣驚呼,稱有龍兵龍將,
聲音刺破少年的夢鄉,他揉著睡眼探頭出艙,
見無邊的鯨陣迎面奔來,在船側不斷縱躍前進,
背鰭整齊如旗,陣勢浩浩蕩蕩,
數不清的巨大身軀壓迫得水面開出條條水道,
真似是龍王出巡的雄壯儀仗,
似乎那巨龍正乘著一輛巨大王輦,隱身在鯨群中央,
又像有無數面戰鼓,被一齊擂得轟隆作響,
水流橫起巨浪,把船隊沖擊得像不倒翁,
不斷左右搖擺,陣陣劇烈搖晃。
這是少年期待的景象,展雄心醉神馳,
奔上甲板,手舞足蹈,
呼喚大鯨馱他同馳共舞,對鯨群縱聲歡叫,
而呆若木雞的水手們聞聽此聲,又莫不失笑,
如同所有平庸之輩,喜把一切不理解的事當作荒唐,
不知道無邪的童聲,正是眾生溝通的旨要,
只認為這些神獸尊從神龍,豈由他一個懵懂少年郎。
而展雄卻清楚地看到,數條長鯨都善意地暼著他,
眸子里都透出清澈的微笑。
此時,所有人都沉浸在這震撼的場面里,
誰也想不到,在鯨群身后的數里之外,
更有數艘倭寇的戰船悄悄圍來,
像是狼群,正向他們的船隊暗暗包抄,
原來倭寇早已得到板橋鎮的消息,
展家的船隊滿載著他們需要的貨物糧草,
而秘密航道,也被內奸在海圖上標注得不差分毫。
鯨群漸漸模糊,終于消失在地平線上,
展雄茫然四顧,滿心悵惘,一時還疑仍在夢鄉,
直到父親暴雷似的聲音再次炸響,
才使他驚醒回首,卻不知竟然就到生死關口。
展祥已看見幾十只倭船和數百個獰笑的倭賊,
震驚之下向大家發出對決的警報。
水手船工錯愕驚詫,紛紛拿起防身的兵器,
領航船上的人,都攏到展祥的身旁。
展老大看著漸漸逼近的如林倭刀,已知在劫難逃,
他臉色鐵青,悲愴地看向面前眾人,面帶慘笑:
“板橋鎮的兄弟們啊,這許多的倭賊
在這里設伏,只能說他們提早得了信報,
還拿到我的航圖,眼前賊眾我寡,
這幾船貨是保不住了,展祥再無顏面去見鎮上父老,
唯有戰死謝罪,把這條老命在此交了。
大伙都有老小,不想死的,就去貨倉
揣上兩瓶燒酒棄船吧,燒酒能暖身可保命,
剩下的事就交給龍王和仙老。”
一位長者聞聽此言,急奔而去,又跑回來,
手捧一具水獺皮的防水衣和兩只陳葫蘆,
水衣是昂貴的遠洋必備之物,可把人從頭套到腳,
葫蘆貌似平常,也是海上救生的法寶。
他是展祥的老管家,見多識廣,謀略頗高,
瞬間已把情勢利析秋毫盤算好,
他目蘊淚光,面朝展祥,強顏苦笑:
“落入倭賊之手,就是他們的肉票,
那板橋的家小還有什么活路?看這許多倭船,
跳到海里不但難逃,反容易被捉到,
還不如拼個死活,去陰間也做個好漢鬼曹!
但也真需要有人活著,把發生的事情傳回去,
找出那個該死的奸細,以免他還禍害膠州和板橋。
另外,這幾條船載的是板橋鄉親累年的血汗家底,
可不能說戰死就一了百了,我輩最重信義啊,
縱然是死,也要善始善終,莫負父老!”
展祥素知管家縝密,拱手請他再講,
管家點頭,就瞥向已然驚呆的展雄,
看著這個自己抱大的少年,潸然下淚,哽咽說:
“雄少爺啊,你爹別無他后,你又手無縛雞之力,
所以不能在這里白送死,無論遭多大的罪,
你也要活回板橋,找出內奸除掉,既要為大家報仇,
更要把眾鄉親的賬還掉,板橋和展門的信義,
只能托給你這個娃娃了,記住,哪怕從此劫難萬般,
刀山刺腳,油鍋煎熬,烈焰火燒,
也要把腰桿挺住,讓人每看到你,都會贊嘆展門英豪。”
老管家扯過神色茫然的少年,硬給他穿了水衣,
把兩只葫蘆綁上,不由分說推向船尾,
眼睛一閉,狠著心把他猛然推下海浪。
展雄驚悸的尖叫,絕望而倉皇,
展祥心如刀絞,切齒舌傷,
眼前驀然黑暗,欲斷肝腸,
他咽下一口猛涌到喉嚨的熱血,
發出如雷暴喊,吩咐各船去做最后的準備,
要把商船變作殺敵戰場,
這時,賬房王繼謀又跳出來,一臉焦急懊惱:
“管家呀管家,你要少爺還賬,卻忘了一件要事,
股份數目都在我的賬上,你要他空手憑何作為?
若有人壞良心報假數,他又如何面對?
快快,事不宜遲,你快去再找一具水衣,
去我賬艙拿賬簿,再系個葫蘆跟他漂回去!”
王繼謀急拽管家,管家擦一把淚,卻對他擺手嘆氣:
“賬簿該由賬房去管,另一具水衣就在我艙箱里,
這是命里該你活著,該你與他同歸,去吧,去吧,
即便賬簿丟了,你也比別人有數。”
王繼謀百般無計,一跺腳奔去后艙。
接下來,就是驚天動地的慘烈之戰,
倭眾把飛鉤掛上船舷,呼嘯著攀來,怪猿惡鬼一般,
水手船工們莫不竭力對敵,同聲咆哮吶喊,
至此無人貪生,皆抱了玉碎的信念,
中國的好漢一旦決意玉碎啊,海天哀嘆,
斷刀與血斧次第墜落啊,仍緊攥在主人掌間。
倭賊勝在勢眾,最后都猙獰圍向展祥一人,
而展祥不愧是展昭之后啊,獨自向前,
肩頭插著倭刃,渾身鮮血,威風不減,
見慣血水的倭眾,覺到罕有的膽寒,
只見展祥從懷里掏出黝黑的火石,
在刀背上猛擦出一串金燦燦的火星,
早已撒了火油的胸前衣襟,驟然火旗招展,
仿佛生出鳳凰的翅膀,在海風中翩然燦爛。
倭眾驚呼后退,而展祥嘴角掛著嘲諷,
踉蹌走入同樣潑了油的貨倉,像是發出火令,
展家的一行商船,幾乎同時燃起沖天烈焰。
倭眾掩面四逃,居然無功而返,
而板橋鎮的好漢們,同時浴火涅槃。
沖天的烈火至夜不熄,
要把警訊告訴附近的漁人,
遠處漁家小兒看到海上的一排火光,
驚呼是龍宮起火并四處叫嚷,
過路的商販三三兩兩把這話帶到板橋鎮,
明天就傳到百夫長的軍門。
匡福將軍聽兒子匡德來講這奇聞,
拍案而起,眼睛里的光芒頓像金色的蛇信,
即刻傳來軍船頭領,這樣下達軍令:
“小兒無知,哪有什么龍宮起火,
這分明是遠洋的商船出了事,
若我猜得不錯,應該就是那大意的展祥
和他的船隊遭遇倭賊,軍船即刻出海,
但愿還能救回幾人。”
軍船頭領有所猶豫,把他的顧慮說出:
“若是遭遇倭賊,此時援救已遲,
駐軍出海,此城必然空虛乏恃,
一旦倭賊趁虛而入,駐地損失,
再有奸人搬弄是非呈報將登大寶的吳王,
只怕壞了大王興致,招致雷霆震怒,
將軍不若安守板橋,明智者獨善其身。”
匡福將軍披掛盔甲寶劍,提起鐵弓,成竹在胸:
“齊地新復,百廢待興,
百姓僅有的財物都押在商船上,
倭賊已截商船,便知板橋財空,
留步卒數人防范細作足可。”
將軍親率士卒,掛帆乘風,
兩個商客牽著一輛販賣綢緞的馬車,看船隊遠去,
相視點頭,載著看不見的陰謀
轉到了將軍的側室、將門之女高秀英的茶館前,
那茶館里架著一張被月老施了魔法的鐵弓,
與匡福的弓正是一對,唯有天定的郎君方可拉動,
將軍昔日偶經茶館,技癢拉成滿月,
鐵弓緣的佳話由此天下傳頌。
如今又有十六歲的女兒若云如花似玉賽仙子,
月老托夢相告,姻緣還是拉開鐵弓的英雄。
南北的豪杰們聞聽,莫不心動,
無不乘興而來,卻始終無人得逞。
出賣展家船隊的內奸,也把此事報給倭賊,
那倭酋是日本南朝第一武士,名叫酒井大郎,
為此欲念大動,心機深沉,欲建奇功,
使兩個細作潛入膠州板橋,偽作綢商,伺機而動,
此時既知駐軍空虛,若是混在羊群的豺狼,
隱在羊皮下的爪牙迫不及待,決定就此出手。
豺狼久在羊群不動聲色,羊群會失去警覺,
細作累日在鎮上叫賣,也深深迷惑了百姓。
高秀英此刻亦不相疑,聽到叫賣聲音,
好心要照顧他們生意,對正讀拳譜的女兒說:
“若云,這拳譜都被你翻爛了,
放下歇一歇眼,去看看那兩個綢商有什么新貨,
如有合適你爹的料子,用你新學的女工,
給他做一件新衣或披風。”
若云答應一聲,放下拳譜,起身出門,
走到街前,仿佛天人降在凡塵中。
兩個細作哈腰諂媚,無比恭敬。
若云低頭去看車上,昔日無異的綢緞,
忽然漾出詭異的香氣,瞬間鎖住她的魂靈,
善良的若云啊,頓失神智,為邪祟所制,
不覺腳步移動,茫然隨車而行,
居然由此步入經年的苦難和噩夢,
待母親驚慌四處尋找,早已不見她的蹤影。
匡福率軍船趕到出事的海面,一無所見,
展祥和船工水手尸骨無存,靈魂歸天,
而商船底艙燒穿,早已沉入海底,從此深眠,
軍船歸途,救起快要凍僵的王繼謀,
卻未曾見到那同樣墜海的少年。
回到港灣已是夜半,忽見高秀英在悲慟哭喊,
聞聲而來的百姓在同情圍觀,
留守的步卒則驚慌無言。
匡福驚覺不祥,急步上前,
失女的母親已撲倒在地,
失魂落魄,淚流滿面:
“相公啊相公,你鎮守海疆,威風八面,
我卻誤信奸人,丟了若云心肝,
有漁家看到那扮作綢商的倭賊,
趁黑把女兒綁上快舟,怕是一去不返,
你快把弓劍給我,再給一船,
讓我去尋女兒,哪怕追到天邊……”
眾將士怒發沖冠,怒吼著就要揚帆,
留守步卒慚愧難當,請求降罪,齊跪在一邊。
匡福目眥欲裂,卻又強忍悲痛,伸臂阻攔:
“倭賊奸詐,詭計多端,諸位不必自責,
莽撞追擊,更也不是良將之選。
我的女兒固然重要,諸將士也有我王顧眷,
我不會為家人,輕易使將士們赴險。
天佑忠臣義士,若云當有上蒼垂憐,
匡家兒女,也不會甘受倭賊之玷,
若云無論生死,都不會辱沒匡家門面。
而倭賊的首級,都將斷于我軍民刀劍,
犯我海疆賊子,有我軍民,必難生還。”
匡福攙起秀英,率隊回營,
同時亡羊補牢,加強戒備,警示全城。
匡將軍愛女若云被擄的消息已令百姓震驚,
王繼謀帶回的噩耗更如晴天霹靂,
膠州老少莫不哀痛,百家號哭,麻布賣磬,
王繼謀來見展妻,匍匐在地,泣不成聲,
表示今后愿效犬馬,來料理展家虧空。
展妻如遭雷轟,魂魄失守,毫無主張,
家里諸事,全由王繼謀代主去行。
卻不知這王繼謀正是那奸賊內鬼,
因妒忌展家的財產,早已與倭賊私下暗通。
王繼謀惡魔附體,敢欺神明,
假作祭奠亡靈,去海邊丟下一只密封的酒瓶,
里面裝有偽造的手書,稱出賣船隊的正是展公,
偽書之陰毒,宛如毒蛇之利齒,
誣指展祥是韃子眼線,也與倭賊茍且,
盜取膠州民財,實為助紂為虐,抗拒華夏新廷。
漁人在海灘撿到瓶子,打開頸封,
頓如毒蠱出籠,蒙蔽了百家股東的心竅,
還有罹難船工水手的家人兄弟,不約而同,
團團圍住展家,刀棒亂舞,吼聲徹空。
展妻從未見過這等情形,在屋里呆若泥塑,
欲要投繯,不欲再生,又念墜海的愛子,
恐其歸來失了娘親,從此沿街乞行。
為此淚水漣漣,左右無定,
而王繼謀踉蹌奔來,跪請主母避禍,
他神色懇切,聲音哽咽:
“黃金白銀迷住了這些市井愚民的眼,
已失心智成了殺人放火的匪徒,
您唯有緊急離開這里,暫去投一家親戚,
最好避得遠遠的,讓他們難以追蹤,
菩薩一樣的主母大人啊,
我一直知道,您是尊貴無比的命,
可不能枉死在此時,受那惡魂野鬼的欺凌。”
王繼謀鼓舌如簧,為她換上仆人衣裳,
不容分說,把這茫然的女人推入密道,
跌跌撞撞,引她由此進入黑暗的前方,
待她知覺饑渴,早不見王繼謀的蹤影,
孤自一人,已在荒郊不知名的路上,
過路的人看見她,都不免嘆一口氣,
可憐她蓬頭垢面,癡呆得不像模樣,
無人知是展家主母,昨日還富甲一方。
她虛弱得走不動,佝腰拾一根木棍撐著,
如此漫無目的地走去,喃喃呼喚著愛子,
她為這連番打擊,已神志不清,
驚懼里唯恐把愛子的名字也忘掉。
匡福看到偽書,明白是奸邪的誣陷反間,
聞知展家遭商民圍攻,急忙上馬帶隊前來,
而王繼謀已頭破血流臥在門前,
捶胸頓足地怒罵不休,忠義滿面,
匡福被他的演技蒙蔽,勒馬對商民們喟嘆:
“僅憑一紙之言,爾等如此發難,
明日說爾是賊,爾等如何分辯?
秦檜曾指岳王是奸臣,風波亭害死忠良,
金人歡呼,遂成千古恨憾,而今倭賊
為禍,最盼華夏內亂,爾等當思,
莫中倭賊奸計,自家骨肉相殘。”
此言醍醐灌頂,商民們如夢方醒,
紛紛收回刀棒,慚愧四散,
匡福將軍令人把王繼謀送醫,
為他包扎上藥,當作義士恭敬禮賢。
王繼謀神色哀傷,心底竊喜無邊,
他的謀劃得逞,以為從此富貴逍遙,
不知道冥冥之中,更有天道之算。
展雄墜海,不久就為驚悸陷入昏迷,
知覺時不知身在何處,也不知還有性命,
頭顱疼得像要裂開,耳畔仍響著沖天的殺聲,
他閉著眼睛,還能看到烈焰和通紅的倒影。
虛弱地向身上摸去,已無水衣和葫蘆,
手足上多了兩副鐐銬,沉重而冰冷。
少年睜開眼睛,發現身處石屋,
一個鼻歪眼斜的丑女坐在對面,打著赤腳,
戴著同樣的鐐銬,骯臟的麻布粗衣爛袖又破領,
她在地上摳起污垢,傻笑著稱是胭脂紅,
美滋滋在臉上涂了一層又一層。
展雄問這是否陰間,還是在夢中,
丑女又害怕地發抖,告訴他這里叫長龍島,
島上住著的,是比陰間魔鬼還兇惡的倭兵,
而戴著鐐銬的,都是擄來的奴工。
聽丑女瘋瘋癲癲地講述,展雄漸知處境,
原來他昏迷中身不由己,隨浪漂抵此島,
而這里早為倭寇所據,是其主要駐扎地,
老管家本欲使他逃離倭寇的魔爪,
誰想他又自投羅網成了他們的奴隸。
少年悲從中來,一時萬念俱灰,默默飲泣,
他墜海后目睹了父親率眾罹難的情形,
清楚地知道倭寇就是殺父仇敵,
痛恨自己沒本事報仇,還淪為倭奴難以逃離。
他雖然還是贏弱的少年,但身體里畢竟流淌著
英豪的血脈,這血脈只能令他選擇寧死不屈。
此時正值清晨,看到第一縷天光,
丑女如見鞭影,拖著鐐銬急忙走出,
為倭寇擔水備皿,佝僂著身子燃灶煮米。
展雄打定主意,拭去眼淚,努力站起,
搖晃著走出石屋,去丑女身旁的木桶里俯身痛飲,
覺得有了力氣,抓起柴堆上的一把斧頭,
在丑女驚詫的注視下,
蹣跚走向響著鼾雷的一排倭居。
巡島的倭兵聽見他的鐐銬聲和帶著殺氣的喘息,
咆哮著奔來,將他踹倒踩在泥里,
怒不可遏地連聲咒罵,拳打腳踢。
少年聽不懂日語,直欲身死魂去,
一心激怒倭兵,這樣破口大罵:
“東瀛倭賊, 大宋名俠展昭的后人,
豈能做倭賊的奴才,來來,趕緊給我一刀,
若我不死,就砍你們的腦袋!”
怒罵引出一干倭眾,為首的就是倭酋酒井,
酒井頗諳華語,聽少年這口吻,
已知是展家少主,不由心中激動。
他正為伏擊展祥船隊未得斬獲而懊惱,
也恨未能生擒展祥,還損失數十卒從,
而他本欲把這名俠展昭的后代征服馴化,
以便宣揚武功,聚攏散兵游勇。
眼下展雄從天而降,使他喜出望外,
認為展祥既死,那就馴化這個少年,
馴化幼小,當然比頑冥的成人更易成功。
丑女在一旁正嚇得掩面發抖,
忽見酒井仰天長笑,宛如狼嚎之聲:
“原來是中國宋朝的名俠展昭之后,
可有本事勝我酒井一郎幾籌?
小子,島上無聊,我們不妨游戲解悶,
若你勝我,就為你取下鐐銬放你離島,
你一日不勝,那就需要老實為奴做工。
看你這樣子是想求一死,但我不能答應,
現在殺你如同踩死一只螞蟻,不值得夸口,
你既是名俠后代,那就該有祖上乃風,
當照我的話去做,信守約定,不然就是背信之徒,
有辱你祖上的名頭。記住,你以后要做的事,
就是或在角斗場勝我,或做我的忠實仆從,
這機會,可不是誰都會有。”
展雄驀然記起老管家的叮嚀,
記起自己還肩負特殊的使命,
羸弱的少年,死欲消退,
心里又生出從未有過的豪情,
一拳擊在地上,咬牙點頭:
“那你就等著,我一定會贏你,
同時請你把賭約告訴你的這些手下,
讓他們都來作證。”
酒井把他的話翻譯給倭眾,
頓時引起一片捧腹笑聲,
都笑這少年自不量力,
居然真敢妄想戰勝日本南朝第一武士,
而這第一武士,曾徒手搏殺吃人野熊,
還曾殺死天皇重臣的近身力士,
在日本無人不曉,一時震動天皇門庭,
他渡海為寇,就是因為天皇律法難容。
而觀這應戰的少年,弱不禁風,
恐怕為奴百年,也無機會取勝。
酒井讓手下放開展雄,陰笑著發施號令:
“小子,在你勝我或發誓效忠之前,
只能去做島上最累的苦工,
身為島奴,鐐銬也只能時刻隨行,
我要在山頂修建諸屋容納未來新眾,
你須每日把采石奴采好的石頭從山下搬上去,
果腹的食物也要自己去尋,
這島上有野菜野果和鼠兔,
也可去海里捕撈魚蝦和海草,
海神對奴隸最為慷慨,
礁石上和海沙里的螺貝四季無窮,
保你這一生都采不盡,餓不死,
只是鐐銬入海容易生銹,
最好能獵到海豹煉出膏油潤護鎖孔,
免得把鐐銬銹在身上,
到時候要效忠也難卸下。
夜里睡覺就跟著那丑八怪,
她雖丑卻也是女人,
你若是思春,就把她給你去消受。”
酒井拎起展雄,擲向那佝僂的丑女,
少年跌在她的身上,不免羞憤臉紅。
倭眾開懷大笑,酒井則又去查看林中密屋
新擄來的女子,正是那仙子似的匡若云,
此刻在那密屋里悠悠醒轉,也是疑在夢中。
若云在榻上睜開眼睛,看著幾個陌生村婦大是困惑
而村婦們見她醒來,臉上也盡是悲戚之色,
她們都是倭賊們掠來的漢家女,因懼倭賊
還殺自己的家人,不敢尋死而忍辱茍活著。
酒井嚴令她們好生看守這個姑娘,不許出絲毫的錯,
少一根頭發,便是事關她們丈夫兒女的生死巨禍。
酒井也警告嘍啰,不許打若云的主意,
因為他要把美人的完璧之身,送給他的可居奇貨,
作為進階去布置他的夢想方略。
倭眾們畏懼他恐怖的力量,覬覦著美人,只能暗捺欲火。
酒井曾于日本妓院浪蕩,與一個名叫山口的青年爭奪妓女,
盛怒下抓著青年舉過頭頂,正嚎叫著要扔下青樓,
意外聽聞那人是南朝后村上天皇的私生子,
馬上化嗔為喜,把山口送到椅子上就座,
妓女讓與他,嫖資也代他付了一年多,
為這嫖資他盜得一城人怒,掌管司法的大臣震怒,
親率力士圍捕,力士的腦袋又被他倭刀砍落,
為此再躲不下去,與山口作別,跪在地上這樣慫恿:
“我的大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神的影子,
你必然要坐到天皇的神位上去君臨天下,
天神讓我遇到你,我就是你實現此事的仆者,
為使你的實力勝過其他的王子,
我要去海上,聚起呼嘯四方的刀客作你的死士,
為大人籌集財富軍費,直取南北島國。”
酒井從此浪跡海上,如野鬼出沒,
以王子特使的身份封官許愿,漸擁數百倭魔,
而他也一心博取爵位,欲懾倭國朝野,
使天下捕快都匍匐在他的腳下,再不能對這盜賊如何。
他由板橋鎮的內鬼,早探知若云之母高秀英與匡福的鐵弓緣,
而令他煩惱的,也是拉開鐵弓即為匡婿的傳說。
山口的野心自被酒井唆起,真就對天皇之位生出覬意,
為此終日禮佛,求佛佑他這私生子獨成正果。
他聞知山口經朝鮮已抵膠州灣,請史臣
講述那里的掌故,又知道那里曾是古齊國的最后守城,
田單曾在那里大破兵臨城下的燕軍一舉復國。
山口怦然心動,認為這是獲得天神祝福的大陸,
遂密書與酒井,要他設計拉攏這里的守將,
以這塊土地為基地,為他廣招兵馬,
然后飛渡日本,像田單破燕一樣橫掃北朝,
使他這私生的王子一統南北,登上大座。
酒井看過密信,異想天開,
欲使山口詭以倭國儲君的名義與匡福聯姻,
認為國丈的富貴當然遠勝于朱家的薄俸,
但既然要拉開鐵弓才可為匡婿,
這誘餌又抵不過傳說的天命,而山口那被妓女掏虛的身軀,
揮舞竹刀都不像樣,只會去抓妓女的酥胸。
酒井盤算一番,遂決定另設毒計,
這才派細作潛伏膠州,行那鬼祟之工。
酒井得意地走盡密屋,就聽到若云姑娘的驚呼,
這時的若云已然明白自己的處境,
欲要躍下木榻,逃出屋去,
而守護的村婦們,唯能硬著心腸一齊把她按住,
同時羞愧地祈禱,懇求天上電母雷公,
早一天顯靈,降奔雷擊殺這些倭賊,
使這姑娘免遭禍害,而她們愿以身作祭,為牢為牲。
神靈沒有回音啊,推門而入的是那倭酋酒井,
他上身袒露著,宛如健碩的公熊,
投向若云的目光,毒蛇一般陰冷。
村婦們看見他,莫不目露驚慌,
如同無助的羊羔,不由地瑟瑟發抖。
酒井沒有揮舞他的倭刀,而是躬身施禮,
他料以若云之姿,必為山口所寵,
既然將是自己的女主,不如盡早
把她當主人伺候,作皇后恭敬。
故此酒井以奴仆之禮,對若云諂媚而語,
又喚仆婦,奉上島上的鮮果珍饈與美酒,
指望若云為其蠱惑,安承此命。
若云是將軍的女兒,頗諳虛實用兵,
見其暫無加害之心,也就少了驚恐,
轉過身去,竭力冷靜,在心里密思百計,
惟可師蘇武之風,既不能即刻逃離,
也只能暫棲狼穴,或能遇到過島的鴻雁,
同蘇武一樣,請鴻雁把自己的消息帶去大陸,
使父親楊帆率兵,將這里蕩平。
卻哪里知道鴻雁也知善惡,能辨吉兇,
寧可繞島遠飛,也不肯見倭刀的光影。
此刻的海浪似在嗟嘆,鷗鳥長鯨皆在哀鳴:
可愛可憐的姑娘啊,她的命運大約天生多舛,
看哪位神靈,會降臨到她的身邊,
給她天使的翅膀,助她飛出牢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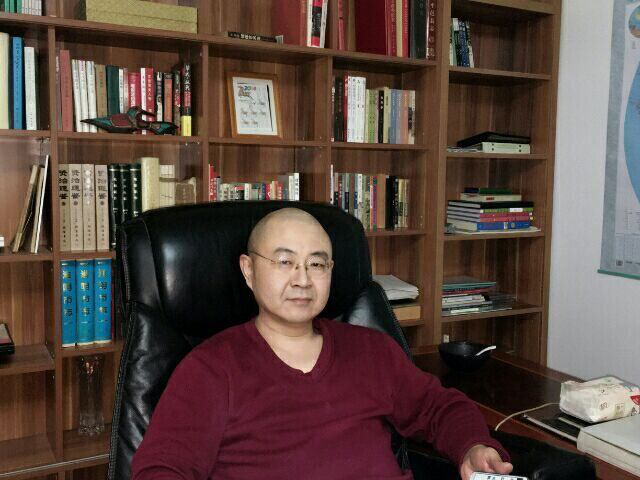
畢云琪:作家、編劇、導演、制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