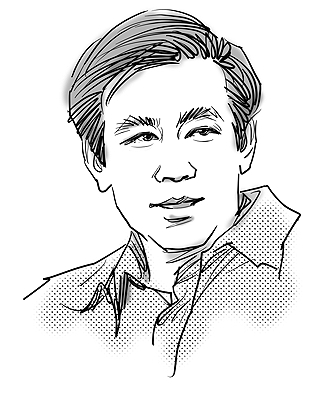 |
| 郭紅松繪 |
什么是散文
很多人認為寫小說的人之所以比寫散文的人少,是因為小說這種文體難以駕馭,而散文似乎就要容易得多。大致來說,我們平時寫的日記、書信,甚至通告和啟事等,都可以算作散文。
事實上,散文這種文體對寫作者的局限確實是最小的。到底什么才是散文?一般認為除了一些情節性的虛構作品,除了戲劇和詩以外,大半都可以稱 作散文——廣義的散文。因為散文的范圍太大太廣了,所以有人曾經提出了“藝術散文”這個概念,認為只有講究藝術性與文學性的、描繪和抒發性的、結構嚴謹的 記敘文字,才算是“藝術散文”。
這種劃分有一定道理,似乎可以看作狹義散文的定義。但是這樣的劃分有時也會使散文在理解方面,多少偏離了它的本質。因為謀篇之用心、法度之 嚴謹、詞藻之講究,又會在一定程度上背離散文藝術的要旨。自然天成、樸素和真實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歷史上留下來的一些散文名篇并不是計劃周密的文章,也 沒有寫作“藝術散文”這樣的意念,結果卻成就了最高的散文藝術。
到底什么才是散文?散文的定義中有必要劃分廣義和狹義兩種嗎?這些都可以重新討論。如果不加以劃分是不是更科學?如果只有好的和不那么好 的、優異的和拙劣的散文,這樣的區別不是更合理嗎?散文史上,有些構思周密的短章美文成為了范本,而另一些似乎不太經意的,或者直接就是為了實用才形成的 一些文字,也成了公認的名作。由此可見,“藝術散文”這樣的界定雖然用心良好,卻實在是有些多余了。
古人的一封辯白申訴信件、一篇自白書、一紙叮囑后代的言論,都成了代代傳誦的美文。它們談不上是構思精密、文法周備的技術主義范本,它們優異是因為寫作者的心胸氣度本來就高,文化素養非同一般。一句話,它的好是從生命本源中流淌出來的。
從這方面看,“散文”是什么可能就好談一些了。它大可以是生活中的一些實用文字,也就是說,之所以要寫它們,那大半是為了使用的。
說到使用,日記書信講演之類好理解,那么抒情的、記敘山川風景的文章呢?后者也可以是“使用”的。因為作者的情感積累到了一定程度,不傾吐 不行。這種抒發也是一種“使用”,而且是一種關乎生活和生存的大“使用”。所以說,從實際使用的目的出發形成的一些文字,往往會收獲最好的散文。而我們以 往對散文的理解正好相反,認為刻意構思出來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這是對文學本質意義的曲解。
一些高境界的散文,應該是或大多是業余寫作形成的。將散文寫作當成一種專門的職業不太好,因為這在具有較高文化素質者那兒,應當是人人必備的一種能力。當然,這也并不是說人人都可以成為散文家,因為他們當中必然有文章高手,有更長于表達的人。
所以小說家、詩人、戲劇家,更有可能寫出好散文來。好的散文大半是他們工作中形成的另一些文字,是自然天成的。其他的好散文則來自另一些人:他們平時在忙一些本職工作,而在工作中形成的、有感而發的所有的文字中,有一部分就極可能成為優異的散文篇章。
寫作的基礎
散文寫作是整個文學寫作的基礎。回顧一下,我們在初中時就學習寫記敘文了,這就是散文。如果一開始就練習寫小說和詩,那會更加不得要領。散 文寫作就是這樣的基礎訓練,先要用文字把事情說明白、把句子寫通順,也就是所謂的“文從字順”。這是很困難的,可以從學習的漫長中看出來。從初中開始就一 直寫散文,可是直到幾十年后,要寫出一篇好文章還是那么難。平時說的“文章”,就是指散文。
就小說家而言,他所倚仗的最基本能力,還是從小時候學習的散文寫作的能力。因為小說中的大多數篇幅都在敘述事情,這就需要一種生動簡約的表 述功夫。小說家有兩大功夫:一是記錄實際事物的,二是想象和發揮的。前者直接需要散文筆法,后者則需要將想象的事物繪制出來。小說家許多時候要有新聞記者 的素質,即能夠直接記錄社會現實生活場景,這有點像通訊報道。這種特質再加上想象變幻的藝術手法,二者疊加在一塊兒,交錯使用,也就形成了通常的小說作 品。
當然,即便是直接記錄的文字,也仍然要有獨特的個性,這與寫散文也是一樣的。質樸的文字不一定就是僵化無趣的。質樸首先就是個人的本色,而 不是重復別人說過的套話。小說中想象和記錄的部分也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無時無刻不在交織的狀態。準確地狀物敘事,把事物以簡潔生動的句子表達明白,這 是最起碼的,也是需要花費長時期的磨煉才能做到的。
小說、詩歌等文體表面上花樣百出,其內部倚仗的仍然是散文的功夫。散文的文字調度手法寬闊如海洋,應有盡有,并不是單調平直的。它在小說的 局部會根據需要改變面目,但無論怎么改變,也還是散文的文字調度技巧。小說家和詩人要有一些特別的詞性和詞序的安排,它似乎是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寫作,但這 種安排一定是建立在對詞性的深刻理解基礎之上的。
一個糟糕的小說作者不太可能會是一個高明的散文家,反過來也一樣。一般來說,好的小說家一定會是好的散文家,而寫不出好散文的人,也不可能 具備創作好小說的能力,同樣也寫不出好的詩歌和戲劇。這是因為抽掉了文學寫作所需要的基礎——基本的和正常的表達能力。再極而言之,連散文寫作都不能完成 的人,有可能是其他領域的杰出人物嗎?這大可懷疑。
現在的流行看法是,如果一個學生的數學、物理功課不好,那么就應該選擇文科。或者說,一個文科特別好的人,往往數學等方面是不太行的。這真 是極大的誤解。其實文字的使用需要的邏輯能力比一般的數學換算還要更強,它簡直無處不在。一個好的小說家要有很強的邏輯能力,搞文科的人,只要能夠走得遠 的,他的數學和物理也必然會是很好的,如果他的邏輯能力一團糟,那么他一定不能成為一名好的寫作者。這個道理很簡單:哪怕極短的一篇文章,從頭至尾寫下 來,都需要經歷無數次極端縝密的判斷。
作文貴在質樸求真
作文貴在質樸、求真,有的人寫文章喜歡用華麗的語言,這大半都是稚氣的表現。現在報刊上的文字,有相當一部分是初級的寫作,但由于傳播的頻率和范圍很廣,很多人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中受到了損害。這樣時間長了,閱歷短淺一點的人就會失去對語言的基本判斷力。
每個時期都有一些套話,這是應該盡力回避的東西,是學習寫作的原則。現在的趨勢正好相反,有人寫文章一定要尋找和使用這樣的套話,并且將此 作為一種能力來炫耀。再就是過多地、不適當地使用一些書面語,對語境不管不顧。有些漂浮的書面語讀了只是在眼前輕輕掠過,沒有具體的分量,沉不到讀者的心 里去。表面華麗的詞語是廉價的,因為它們不需要尋找,就擱在那兒。從心底流淌出來的文字才感人,因為它們是經過了心靈過濾的。最常見最普通最不時髦的詞匯 不見得就不好,反之也一樣。詞沒有不好的,就看我們用得好不好。
漢語中最有力量的詞是名詞和動詞,它們是語言的骨骼。語言的虛浮臃腫,主要原因是形容詞之類的用多了。句子像人一樣,要減肥,要干練,這才出線條,才帥氣。追求美,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沒完沒了地抹化妝品,只會適得其反。
有人誤認為散文與小說不同,是需要搞詞藻比賽的,這非常錯誤。什么文體都是簡潔而后生動、樸素而后華麗。有的素質不高的企業家發了財,想請 文章大家給他寫點歌頌的文字,于是就有這一類寫手去吃他們的“豆腐”,辦法就是從字典上找一些詞兒堆積起來。企業家一看這么多詞,而且聞所未聞,一下就折 服了,以為遇到了真正的“文章大家”,就慷慨地付給很多錢,以為物有所值。其實這都是騙人的伎倆。
在文章中,使用一個觸目的偏僻的詞,往往是十分困難的事情。這就好比一個硬塊來到了語言的水流里,需要更多的浸泡才能融化一樣。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回避它,不到萬不得已不要使用。
有一些不好的習慣是小時候帶來的。從開始學習作文時,老師就千方百計讓我們用詞,用上一個成語、一個詞,老師就畫一個紅圈以示表彰。為了得 到更多的鼓勵,我們也就絞盡腦汁往上堆詞。小學生的行為,卻會保持到成人時代。如果我們更早地遇到一個老師,他告訴我們自然樸素的重要,告訴這樣才能走到 文章的高境界,那會多好啊。這樣就不會以辭害文了。
真正的文章高手都是挺倔的人,他們心氣高,平時不會采用被人頻頻使用的時尚套話。人在作文這種事上,最起碼要有自己的語言方式。現在只要展 開報刊或文件之類,就會發現都在說一些大致差不多的話,這讓人覺得掃興和窩囊。來到了一個什么地方啊,到處都是鸚鵡和八哥。其實仔細想一想,我們做人的自 主和自由,就得從說自己的話開始。
從大處著眼,人生其實不過是一篇文章而已,有起承轉合,有段落,有主題思想,也有開頭和結尾。散文與我們的個人生活也許貼得最近了。改變語 言方式,可能從寫散文入手是最合適的。廣義的散文遍布在我們的四周,寫作是怎樣的,生活就是怎樣的。每個人把自己的文字修理得干凈了,生活一定會發生改 變。當假話、套話、時髦話滿天飛時,這個世界肯定不會讓人幸福。欺騙總是從語言開始,以受騙者在現實生活中的痛苦告終。
小說家的繼承
中國的小說當然要繼承自己的文學傳統,但中國文學史上最發達的還是散文和詩歌。“詩書之國”,就指了詩詞和諸子百家。翻開以往,更早的時候幾乎沒有可以稱為小說的東西,再晚一點的只是一些傳奇和通俗故事。志怪小說似乎不能作為當代雅文學的源流。
不過由于文學的核心不過是一種詩,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小說仍然有最豐富的文學遺產,這就是古代的散文和詩歌。從外部形式上看,好像可以從 古代借鑒的不多,如果從精神內容上看,就應該古今一線貫穿下來。古詩的精神是當代小說的核心,古代散文的筆法氣質更是當代小說的基本構成。古代還有一種介 于小說與散文之間的“筆記小說”,更是讓今天小說家直接領受的一筆遺產。
《史記》開辟了中國史筆的先河,是記敘的典范。它議論精當,敘事簡約、深刻、生動。它兼有散文和小說的主要元素,既是今天散文的源頭,也是今天小說的源頭。后來中國的歷史典籍受它影響太深了,形成了議論概括和生動描敘的傳統。這也是中國情節虛構作品最好的范本。
由此看來,中國的小說和散文結合緊密,二者離得非常近。實際上當代雅文學小說的世界潮流,并不是越來越離開了散文,而是進一步趨近求同了。 像國外的一些著名小說作家,如米蘭·昆德拉、索爾·貝婁、穆齊爾、庫切……他們的小說散文氣質濃烈,最嫻熟地使用著這兩種文體。
而一些通俗小說,離散文有點遠。通俗小說最重外部情節的曲折驚奇,以便吸引讀者。雅文學小說的寫作則一直靠近散文。散文的“散”,一般來說 主要是情節意義上的“散”,而雅文學小說也并不僅僅以外部情節的緊迫取勝。就這一點來看,當代雅文學小說與散文有極大的一致性。
這就可以明白為什么好的小說家必然是一個好的散文家的道理了。看一個小說家的素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看其散文隨筆的寫作水準。邏輯思維的強 大并不意味著會淹沒其感性空間,因為淹沒的原因仍然是邏輯把握力的欠缺。小說家在感性空間里放縱自己時,就像飲了過量的酒一樣,心里應該還是有數的。這個 “有數”,就是指邏輯的把握能力。再多的酒還應該“喝在人的肚子里”,這是人們對酒后無德者的諷刺,這里用在小說寫作上,不失為一個貼切的比喻。
比起散文,小說的虛構性從語言上看要強得多。但這并不是說散文的語言就一定是直接從生活中搬來的,這也不可能。所謂語言的虛構性,是指作家 的語言進入創作之后,已經是他個人的了,不與任何人相同。如果他的語言像大眾、像現實中的人物說話,那也只是一種貌似而已。我們常常說的作家的“語言風 格”,就是寫作中的語言虛構,它是一回事。
那么散文呢?它又留給我們多少虛構的空間?前面說過,散文是人人都可以運用嫻熟的一種文體,那么人人都具有虛構的能力嗎?當然是這樣。根據 寫作的進入程度、深度不同,這種虛構的能力也不同。這樣,等于說作家要有自己的語言方式,而這種方式是逐步煉成的。與小說的虛構不同的是,散文在事件(情 節)人物方面的虛構余地不會太大。因為散文要真實,不能杜撰和編造。但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記述,這和小說家又是一樣的。
(作者為山東省作協主席,著有《你在高原》《九月寓言》《古船》等)


